第二十九章 西方世界 (1914~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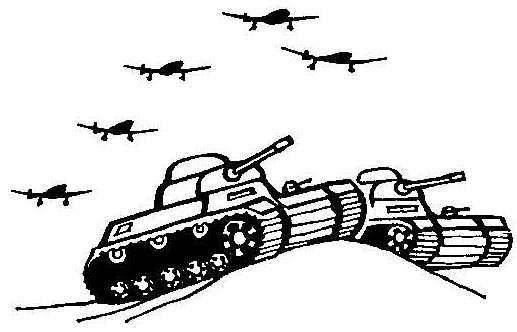
被短暂而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所隔开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一样加速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也将西方社会导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别是在激烈的冲突下,为进行战争而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障碍被排除了。随着政府逐渐发现专门致力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战时“指令经济”效果十分明显,一种有意操纵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战争的一系列可能性开始显现。因此,各个政权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都在根据这一计划努力地重新引导人类和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认可了一种发现:像政府一样,经济和社会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被说服或被迫服从某个人的命令,根据一些人的命令执行,它们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至少在宽泛的局限性之内)。
在1815~1914年间,一种不同的思想和实践界定了我们确切地称之为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与19世纪自由主义宪法的制定已经清晰地表明,政治体系不是通过自然或上帝赋予而是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有改变的意愿,它就可以被改变。另一方面,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认为,社会和经济是自然产生的,超出意识所能控制的范围。他们认为,公共税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为不会对由人类天性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关系所界定的各种人类生活方式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有社会主义者预见到通过政府行为来大规模、有意识地重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但20世纪实际已经实现的状态与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后的社会期望似乎相差甚远。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西方历史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分水岭。在战争的四年里,交战国政府盲目而不顾一切地探寻新的动员社会—经济的有效方法。战争的影响削弱了阶级和地区的差异,因此,到1918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所有西方的主要工业国家中都显现出了一种新颖的、后资本主义模式大众社会的迹象。
人类的思想也被深深震动了。没有人预想到工业化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并且充满着血腥的杀戮。这足以让人们轻易地否定早在1914年以前就遭到质疑的进步和理性的信念。但是能够取代这种过时的18世纪对人类境遇的看法的信念很难达成一致。在20世纪前半期没有出现公认的一致看法,尽管出现了新生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爆发的。没有哪个欧洲政府希望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另一方面,除意大利之外的主要欧洲国家,在面对敌人的外交挑衅时都倾向于战争而不是退缩。
将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联盟模式比起其他形式,让双方都显得更加缺乏变通。冒离间联盟危险的退缩者或许会得到进一步的挑衅。因此,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塞尔维亚(或整个巴尔干半岛)对德国有利害关系,而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国唯一能够指望帮助其抗衡协约国(英法俄)包围威胁的盟国。基于同样的考虑法国和俄国结盟。当法国的利益没有被重点照顾时,它只能以证明自己是俄国一个忠实盟友的方式在之后的危机中支持俄国而反对德国。
欧洲卷入战争的第二个因素,是各支主要军队所制定的几乎无法改变和控制的动员计划。根据这些计划,要从平民中征召数百万的预备役军人并配发制服和武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运往边界。荒谬的是,根据这一计划,每一列火车都要小心使用,对计划的任何调整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每件事都很好地同其他事情协调时,中途的任何一个中断都很容易造成混乱,而一旦混乱就会导致军事失败——这正是动员计划所设法避免的。
因此,一旦俄国命令全面动员(而且他们“必须”这样,因为他们比敌人需要更多时间将军队集结在边界),奥匈帝国、法国和德国就会次第被触发而迅速地发布动员令。这种自动性取代了政策,军事领袖取代了文官领袖;动员计划转变为战争计划,没有谁真正决定这样做,因为敌人的军队是“根据计划”开始迅猛地开往边界。
而这种预先精心安排的沿着边界线梦游般的军事计划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只有德国的“施里芬”计划经受了实践检验。这个计划要求德国将重兵集结在北部临海,集中大部分兵力打击法国。为了在之后能够集中打击东部的俄国,这就要求德国在战争开始的几周内就要围攻巴黎、击败法国。但是德国人认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通过比利时,因为被严守的法德边界使得德国不能按计划快速通过并取得胜利。而宣称比利时永久独立的1839年条约为此造成了不便。但在1914年这种已经显得过时的“一纸空文”对于德国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另一方面,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只不过是为英国政府介入战争反对德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借口而已。这也让同德国和奥匈帝国有防御同盟的意大利更容易地认为,自己无须承担参战的责任,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并没有遭到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