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南极!南极!(第4/10页)
我能做的,只是搂过梁红。我是她最后的依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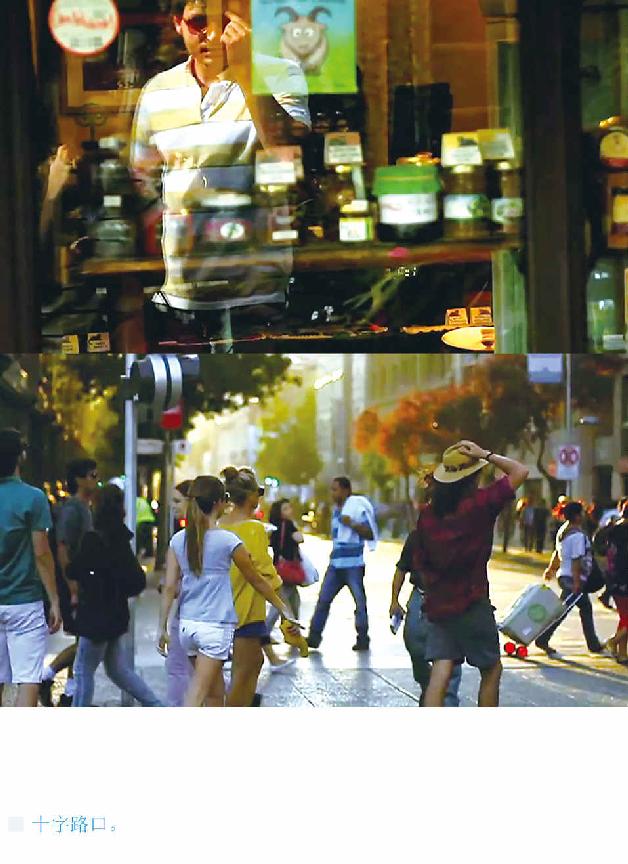
命悬沉船湾
在圣地亚哥,跟几个要离开的船员一一拥抱,告别。
“小宇你别把自己给弄丢了。回家好好陪着你妈,替我们给二老带个好。”
“老陈你路上照顾着点儿小宇,过关的时候别跟人海关较劲儿。”
“魏凯回去了好好陪陪闺女,别再大大咧咧的了。咱们回北京了去看她。”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离愁别绪之中,梁红再次失语落泪。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他们,魏凯、小宇、老陈。没有他们,我们连智利都到不了。每个人做了多大的贡献不论,能够一起出来,船上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其他人咬牙坚持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不相信他们是真的放弃了去南极这个梦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多避不了的牵挂。他们人虽然不在船上了,但是接下来,“北京”号还要带着他们的梦想和祝福,一起去南极。
曾乔被我强留了下来。“咬咬牙,希望就在前方。你他妈真要跑了,海里淹不死你,我也打死你。”纠结了半天,曾乔终于还是点头了,留下。但是他跟我较劲儿似的,全心静养腰伤,不干活儿。
三个人去不了,我从北京又火速招了两个人来驰援。一个是多年的朋友老布,一北京顽主,天不怕地不怕,跟阎王爷也敢呛几句。另外一个是球球,梁红的侄子,一小孩儿。他妈推荐过来的:“这孩子太宅了,别的孩子这个年纪都离家出走了,结果他还天天待家里玩游戏。你们带他出去见见世面,让风雨锻炼锻炼。”
新人来旧人走,船上沉郁已久的气氛又热闹了起来。球球三岁到十九岁,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没什么新鲜的;老布从穿开裆裤到混成京城一魔,则有说不完的故事。再加上祖上那点事儿,说上几个来回,够我们消遣到南极的。
各忙各的一天,到晚上球球才提起:“船长,今儿好像是过年吧?”
一翻日历,还真是。“咱也别省着了,船里的好吃的好喝的,都翻出来,摆上,咱们过年啦!”
春联贴上船舱,有点儿过年的喜庆味道了。罐头、零食、饮料,堆了一桌子,没多少是吃下去的,都互相撒了。一顿肆无忌惮的笑过后,所有人都沉默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梁红的眼里已噙着泪花。两年了,去年的春节,我们在奔赴奥伊米亚康的路上;今年,我们又在去往南极的海上。
“开网,该打电话的打电话,该发短信的发短信,给家人、亲戚、朋友们,报平安。”
出了圣地亚哥,为了抄近路,我没有选择走太平洋深处,而是沿着南美洲的大陆架,在蒙特港进了智利峡湾。
我的这一次选择,几乎就把“北京”号葬送在峡湾里了。
起初一路还算顺风顺水,在智利峡湾里,边行边游。两岸嶙峋的峡谷,姿态万千,几万年来的自然形成和风化侵袭,造就了它们鬼斧神工的模样。虽然峡湾里暗礁众多,但是小心行事,伴着两岸美景,这一路走得很惬意。
走到峡湾中段的时候,有一个东向往智利内陆的分叉。烟斗的信息说,走进去往回绕一程,能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一例内陆冰川。
这种地方,我绝对不可能任其在我手下溜走。转向,走向峡湾的更深处。八个小时的航行,怪石岩壁的尽头,是一堵皑皑白岭。在我们的认知里,冰川只存在南北极或周边地区的海里,眼前却是一座在峡湾深处的内陆大冰川。除了颜色变化,冰川的冰壁险峰,与两边的大峡谷一样奇峻险兀。不同的,是它的洁白里,让人远远看着都透着料峭寒意。
峡湾里无处停靠,我和梁红先放小艇上了冰川。站在不知几百米厚的冰岩上,望着头上巍巍巨凌,伸手摸一摸,千万年前的彻骨极寒,瞬间沁人心脾。冰川仿佛有蛊惑人心的魔力,宁静、空明。闭上眼睛,脑海里仿佛我在随着冰川漂移,天空风云变幻,我随着冰川穿越千万年的历史,沿向无尽的时空旋涡里。
“天快黑了,要让每个人都上来感受一下。”我和梁红依依不舍地回到小艇,上船,换老布、曾乔和球球登陆冰川。“随时可能冰裂,动静不要太大,别大声说话。”我交代着。
他们似乎也被壮观的内陆冰川震撼到了,上去后,走几步,都中邪般呆立原地。抬起头,闭上双眼,张开怀抱,拥抱着身前的震撼和虚无。
回到船上,我们折返回去,沿着峡湾继续往地球的最南端进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北京”号触礁了。
出海一百九十六天,大风大浪,磕磕绊绊,“北京”号早已千疮百孔,但一直没有抛弃我们。从香港到东海,从济州岛进入日本海,过宗谷海峡到鄂霍次克海,再到白令海,沿着美洲狭长的海岸线到这里,它载着大伙儿航行了两万多海里。这次,“北京”号遇到大麻烦了,行驶到智利峡湾最后的一段路,我们闯入了船只墓葬群。GPS和海图配合错误,船经受剧烈的一撞,半截直接跑到一小岛上去了。“坏了,船要沉!”老布翻身起来就往底舱跑,查看有没有漏水。